低浓度苯的职业危害及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biomarkers of low-concentration benzene
-
摘要: 职业性慢性苯中毒是有机溶剂中毒性职业病中占比最高的一类职业病。由于近年的工业升级改造,化工生产都改以低浓度苯作为工业原料,但苯的低浓度使用并不能完全消除其对健康的危害,反而给职业危害预防带来更复杂的考验。综合国内外文献,综述了苯对人体神经系统、骨髓造血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皮肤、肝脏的损害和致癌作用,分析了苯的暴露标志物、效应标志物、易感性标志物等,认为在进行苯中毒的防治时,需尽快探索出针对低浓度苯的职业危害的一系列综合防治措施,包括寻找到准确可靠的早期诊断效应标志物等,以期为低浓度有机溶剂暴露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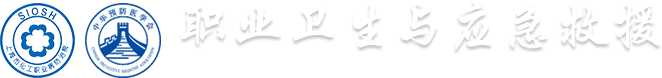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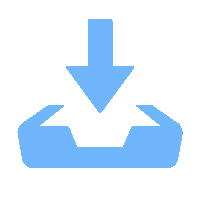 下载:
下载: